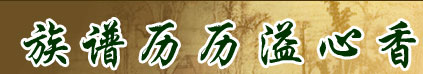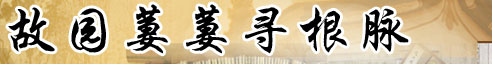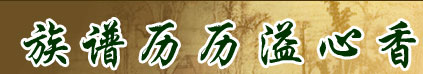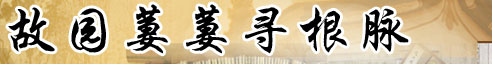南京城西莫愁新寓一棟陳舊的單元樓中,上世紀40年代就享譽藝壇的金石篆刻大家石學鴻老人過著隱于市的平靜生活。防盜門上方高懸石老自題匾額:“厥廬”。“‘厥’者掘石也,貼合金石篆刻之意。”石老說,“它源于我家一部續了2700年的‘厥’字號石氏家譜。” 清代家譜記載2700年家族史 在斗室北墻的壁龕中,石老顫巍巍地為記者取下了這部刻印于1886年的家譜。
打開裝幀精美的錦盒,它呈現在記者眼前,上下共四冊,按照“孝、悌、忠、信”的順序整齊地碼在一起。線裝、木活字印刷、毛邊紙……每冊封面題為“武威石氏蚺城宗譜”,其下一方朱文印“厥”字。石老手指“厥”印表示,堂號“厥廬”便源于此。
石老為記者介紹,這部石氏家譜記載的第一位先祖是春秋時期衛國的大夫石,他住在今天的甘肅武威,因此武威也成了石氏子孫的祖籍。明清之際,石氏79世祖遷居到了蚺城(今江西婺源),清中期石老所在的一支又遷居到南京。1886年,婺源石氏續修家譜,所以名字叫“武威石氏蚺城宗譜”。石老的祖父也參與了這次盛會。家譜修好后按照“自、今、以、始、蕃、衍、盈、升、克、昌、厥、后”的順序刊印了12部,厥部便被石老的祖父帶回南京,到了現在正好整整120年。石老告訴記者,從石到他自己,這部家譜上記載了2700多年來石氏的家族變遷,比曲阜孔氏家譜記載的還要長200年,可能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家譜了。
保護家譜歷經坎坷
對石家來說,失了家譜便是斷了根,因此無論何種磨難,一家人都把保護家譜視為第一責任。1937年,日寇進逼南京,石學鴻的一個堂哥抱著家譜躲進漢口路的國際安全區。后來覺得不安全,石學鴻抱著家譜一路跑到六合八百橋,日寇追來后,石學鴻急中生智爬到路邊草垛中,躲過一劫。石老說,日寇攻陷南京后,他位于十八街的家中被洗劫一空,祖父畢生搜集的古籍珍玩片羽無存,所幸家譜尚存,根未斷。
因為父親早逝,石老直接從祖父手中接過了這部家譜。“那是1947年中秋,全家團聚于南京朝天宮西街家中,祖父親自將這部家譜交到我手上,告誡我要好好保存,傳下去。”然而解放后由于歷史原因,石老被關進監獄20年。“文革”期間石家被抄,浩劫之后一位路過的老漢竟在路邊撿到了這部家譜,將其上繳到徐府巷居委會。1975年,石學鴻出獄后幾經尋訪,竟然再次索回了這部家譜。“這真是天意啊!”講到這里石老連連嘆息。
傳下去是最大心愿
記者了解到,當年石氏刻印的12部家譜如今就只剩下了石學鴻這一套。“文革”之后,全國各地的許多石氏子孫都來這里查家譜,石老還做了一本“宗譜摘錄”送給來尋根的石氏同宗。石老說,家譜不但能加強同姓人的聯系和凝聚力,還教給他們為人的道理。這部家譜中既有石大義滅親、石奮父子世代為官這樣的忠臣名士的故事,也有石崇斗富終至身敗名裂的教訓,足以警醒石氏后人。 在寓所中,石老把自己畢生的金石篆刻作品全部擺在家譜四周,呈拱衛之勢。他說,在自己一生中最重要、最費心血的便是這本家譜,現在自己老了,最大的心愿就是家譜能好好傳承下去。
(來源:南京日報)
編輯:秋日 |